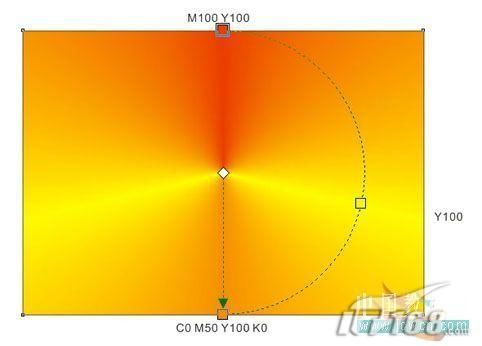萬盛學電腦網 >> 圖文處理 >> 平面設計理論 >> 如何理解日本禅和日本設計?
如何理解日本禅和日本設計?
這是我們《NO ART》雜志的原創內容,原文標題為《被設計的禅》,刊發在雜志第三期,文章經授權在壹讀發表後廣為流傳。

關於日本禅和設計,我們都想錯的。
日本人其實對禅沒有什麼概念,禅這個東西可能是日本國以外的人強加給他們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沒有那麼多人天天在說禅,即便是曹洞宗的和尚也沒有天天說禅的。因為所有的這一切,簡潔、干淨是日本的根本,所有的東西一簡潔、一根本之後,就能夠套到很多的道理裡面去。
禅是佛教所有派系裡最特別的,它不利用文字,它是瞬間的很簡單很直接的東西,你明白了就明白了,大家斗的是快速反應,但現在對禅理解的誤區就在於,覺得畫得少一點、寫得空靈一點、布置得簡單一點、留白多一點,那就是禅。那是兩回事兒。

川濑敏郎的插花寧靜而雅致
其實日本的花道、茶道也好,劍道和香道也好,它的簡單、簡潔不是禅,是生死。
比方說劍道,無論是上中下哪一段起手,它講的都是不要浪費,要最快出擊,而且它不是說擊倒就完了,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日本的花道也是,不像在中國,一插花,就看你拿的是什麼花,他拿的是什麼花,日本人比的不是這個東西。茶道更是如此。現在國內大家都玩巖茶,因為巖茶經過火焙,工序多,中間的說法就會很多;普洱就更加講究,完全屬於喝年資,就是說你這一代做的普洱你自己是喝不到的,可能要到你的孫子那一輩才能喝到。歸根結底,都需要有資源,你才能壓得起、積得起、玩得起。但日本沒有那麼多資源,它幾乎都是山地,越往內陸走越窮,到現在都是這樣。因此日本人沒有多余的東西可以浪費,必須精致地來做。這種環境影響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最後又變成了他們的習慣,這個是最重要的。
生死

很多人說,日本的這個是中國的,那個也是中國的,這個說法其實挺可笑的。它是中國的,但你必須加上“曾經”這兩個字,而這個“曾經”你是找不回來的,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辦法讓它變成你的習慣,你更沒有辦法讓它瞬間變成你的思維模式,最後你找回來的只是一個形式,就是一個古董。這些東西在日本還留著,但代代相傳之後,它的體系跟中國已經沒有關系了,所以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一樣的,它所體現出來的是浪費不起,因為浪費不起,就做得很干淨。

日本劍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國漢代的家具很簡潔,而且有勁,那是基於它的料足,到了明代,料也是很講究的。但你看日本,它沒有那麼大的料,進口又進口不起,運也運不回來,那怎麼辦呢?所以唐宋之後,他們也要找他們自己的東西,這個時候,出來了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千利休。


茶具
千利休的文化不是簡單的禅文化,千利休是武士,而那個時代日本是沒有什麼文人茶的,都是武士茶,因為它要影響的是領主。對於領主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開疆辟土、保家衛國,而且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每一次出去,你都不知道自己回不回得來。所以將軍幕府要讓自己時時刻刻保持冷靜,在這一點上,他那些將士是幫不了他的,那就由茶人讓他冷靜下來。這才是那個時代的茶的根本。
所以你看千利休的茶室,只有兩疊榻榻米那麼大,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喝茶。人們在有距離的時候才能放松,而千家茶就是不讓你放松,反而要讓你極度緊張,因為它要的是對峙,兩個人在如此近距離的對峙下,你還能保持冷靜,能夠非常有序地把一套儀式化的程序保持下來,那就是你的本事。千家茶的根本在這裡。當然,天下太平之後,茶道就出現了流派,演化出了不同的游戲規則,但是,決生死這一點到現在還是一樣的,不管是裡千家、表千家還是武者小路千家,都看你能不能很冷靜地把那一套程序演練完。

安籐忠雄作品《水之教堂》

安籐忠雄作品《光之教堂》
從這一點去看,你看建築師安籐忠雄,他不是武士吧?但是他的設計最後所追求的那種利落的感覺,跟刀口又有什麼區別呢?安籐也好,隈研吾也好,老一輩的丹下健三也好,其實是沒有區別的,只不過是呈現手法上有區別而已。
又例如服裝,老一輩的三宅一生,他的邊線的處理極其利落;山本耀司看起來夠繁復了吧?但你看他的整體利不利落?一樣利落,他用黑色把所有繁復的細節和變化都統一了;川久保玲也是一樣,都是同一個道理。
再比如國人最熟悉的無印良品,它也不是禅,跟禅沒有任何關系,它其實是整理,整理到最中性。從廣告的角度來說,它非常注重材料的干淨,但它真正追求的其實是整理和秩序,只有靠這兩點,它才能把商品賣到全世界去,因為它已經把所有的裝飾的成分減到最小,它不需要那些極具故事性的裝飾,它的哲學是,當你把裝飾去掉,還原它的原型的時候,那麼東邊的東西就可以拿到西邊賣,西邊的東西也可以拿到東邊來賣。
所以這樣一條線捋下來之後,你就會發現,日本的禅是功能性的,而中國的禅是趣味性的,這兩者不是一回事。
空白

禅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幾年中不斷被問及,但在中國談論這個問題的幾率遠遠高於日本,日本人就很奇怪,比如原研哉和深澤直人,說為什麼我一到中國,大家就要問我跟禅有什麼關系。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種習慣,但中國這邊因為有這樣一個傳統,所以需要找到一個點去看日本。

無印良品海報,原研哉作品
其實原研哉的白是繼承他的老師、武藏野美術學校的向井周太郎,後者整理了一整套形式上以白為理論基礎的體系,原研哉繼承了這個,更通俗地把這個白說出來了。你看日本的白色的樟子門,纖細的木條,白色的紙,你打開就是一個世界,關上就是兩個世界,中國人會覺得非常神奇或者好玩,但日本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深澤直人設計的CD機
禅宗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立地成佛,就是一針見血,它是減到底,那麼,減到底之後,你放到哪裡都是一樣的。比如說把北歐的家具和工業設計拿出來,你會覺得它比日本禅得更徹底。所以禅最要緊的就是你跟根本原理之間的距離有多遠。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禅又是非常中國的,它在印度產生不了,因為太虔誠的地方是產生不了禅的;而在中國,它是逃跑保命的哲學,例如打坐,我坐不了那麼長時間,那就不坐;但是日本又不一樣,它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你去看日本的國花就很清楚——一年365天,櫻花的花期就一周時間,就是說360天你都在等待,然後有五天櫻花全開,最後“嘩”一下全部掉沒,你是看不到櫻花敗在樹上的。中國呢?你看牡丹花,慢慢地長,慢慢地謝,從最好看到最不好看的階段,你都要去欣賞它,這跟日本完全是不同的兩個思維體系下的東西。那回過頭來說,中國和日本的禅都是禅,只是方向不一樣、手法不一樣,所以說,禅是無形的,它沒有一定之規。
說到這兒,似乎可以結束了。但如果非要接下去,那我們也可以說,禅其實也是有形的。它體現出來的是干淨、利落、明快、清新,體現的是思維的完整、體系化。

梼原木橋博物館,隈研吾
你把日本的設計和北歐的設計放在一起,同樣干淨利落,為什麼依然能分清?就是因為日本在干淨利落的形式中,還有抒情的成分,而北歐是無情的、禁欲的,它的家具完全是從功能出發、流水操作,沒有抒情的;但日本不是,日本是家族作業,在選料和制作的過程中,會有自己的趣味在裡面。我們可以說,萬物皆禅,日本人也在很努力地接近材料的本質和功能的本質。
所以,日本設計的極致,跟萬物有靈論關系不大,主要就是因為可選擇的材料太少,他浪費不起,因此必須在有限的材料裡做到極致。在平面設計上還不明顯,一到建築和家具設計,成本控制就顯得非常要緊,所以就導致很多設計師用不了好材料,拿不到好材料,最後只能盡量用身邊的材料。
而且,當我們說日本的極簡主義的時候,它跟北歐的極簡也不是完全一樣的,只能說它們是暗合,就是當你用這樣一條思路去做設計的時候,做出來的就是極簡的。所以日本的設計乃至整個美學觀念,反倒可以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

三宅一生作品
你看三宅一生就是這樣,他是日本時裝設計圈裡對材料開發最厲害的一個人,對隈研吾等建築設計師的影響都很大。他認為材料不是遠處求的,而是你身邊就能得到的,所以隈研吾也不會像安籐忠雄那樣,你不給我76號標號的水泥我就不給你干了,隈研吾的東西五花八門,不是說他刻意這麼做,而是說他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這是隈研吾最大的禅意。
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是禅,關鍵看你是不是能自圓其說。日本和北歐都能把自己說圓,中國不行。原研哉最牛的地方在哪兒?他的設計在日本至今也不是一流的,或者說不是一流裡面最好的,但他的理論體系是最完整的,就像一個容器,什麼東西我都能往裡裝,那你就沒法攻擊它。和尚為什麼坐在那兒嗡嗡嗡嗡地說?原因就是讓你成為我的粉絲,我給你洗腦,怎麼洗?你邏輯上首尾相連,人家找不到破綻,就覺得你說得真有道理。佛教也好,道教也好,那都是空手套的爺,是皮包公司的爺。

川久保玲作品
至於哪些日本設計師算是好的設計師,這個問題太大,無從說起。但那些活躍在一線,理論上又能首尾相連的,我的書裡提到的那幾位,像三宅一生、隈研吾、深澤直人、原研哉、佐籐可士和,都好。安籐忠雄也是好設計師,但我在選擇隈研吾的時候就注定敵對了安籐忠雄,他們在和自然的關系、呈現方法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不過,站在安籐的角度看,他的作品還是很優秀的。至於矶崎新,他的作品遠不如他的理論,他是日本很少有的能做宏大構架的建築理論的建築師。
日本設計在國際上地位這麼特別,跟它的體系清晰、風格明確有關,也跟他們的教育有關。比如說干淨,我們說起來很容易,但干淨其實很難,保持干淨清潔真的近似一種修養,但是日本人,尤其是老一輩日本人,他會給自己一個規范,例如知道自己要七點鐘出門,可能五點半就起床了,收拾清理榻榻米,打掃房間,整理衣服,等等,這種自律和自我約束最後影響到日本的方方面面,包括設計,那這些東西算不算禅呢?都是禅。
- 上一頁:回味那些青峰筆下動人的文案
- 下一頁:專注無縫紋理素材站+多邊形背景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