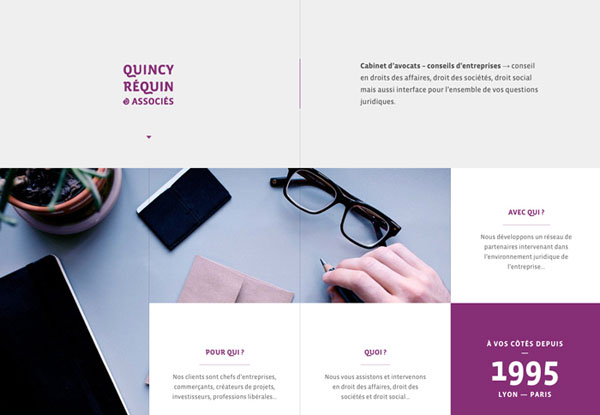萬盛學電腦網 >> 圖文處理 >> 平面設計理論 >> 平面設計在中國
平面設計在中國
平面設計在中國
時光荏苒,似乎剛剛寫完那篇《2004:中國平面設計的一些事》(見《藝術與設計》2005年第4期),轉眼之間又到了該為2005年寫點什麼的時候了。“2005”決不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一個平凡的年份:中國電影百年、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周年、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一個世紀的文化風雲,似乎都要不約而同地等到這一年中來總結。相比之下,平面設計的圈子裡也是倍加“熱鬧”:從夏天的“溝通”展到“2005中國國際海報雙年展”、“故宮會徽”引發的爭議,以及奧運吉祥物的最終公布和深圳市平面設計協會重張復會後的“亮相”——“平面設計在中國05展”,這些似乎都應該繼續記載到我們還沒有完成的《中國當代設計史》中並加以反思。無論如何,繁榮與丑聞並存,專業設計師與政府的分歧日甚,各地設計師組織的對立大於合作,這些現象對於至今並未真正形成的中國設計群體和設計師組織來說,都不是什麼值得歡呼雀躍的事。
一、“抄襲”:2005中國平面設計的公眾印象
在以往,大概除了“奧運會徽”這樣關涉政治的設計事件,平面設計小圈子內部的分分合合都很少能夠得到公眾的關注,就連“AGI中國大會”這樣的“盛典”也概莫能外。2005年則不同,除了情理之中的“奧運吉祥物”的大量報道之外,關注主流傳媒的人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中不難經常遭遇到平面設計界的報道。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報道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與“抄襲”這樣一個並不光彩的關鍵詞聯系在一起的。先是安徽工業大學設計系教師朱巖岳公開指責老設計師邵柏林和理想公司設計的故宮博物院院徽有抄襲其參加征集的方案的嫌疑,並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理想公司告上法庭;緊接著浙江財經學院設計系教師林洲在杭州《第二屆中國國際海報雙年展》上獲得“全場大獎”的海報被網民指責為剽竊外國設計師創意,並提供了極為強有力的圖像證據。一段時間以內,不僅僅是設計界的專業期刊和網站,就連中央電視台、《北京青年報》、《新京報》、《京華時報》、《北京娛樂信報》等大眾傳媒對此也表示出極高的興趣,一度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平面設計這個容易被人遺忘的角落著實被公眾關注了一把。
直到筆者寫作這篇文章的2005年12月24日,“第二屆中國國際海報雙年展組委會”於2005年11月2日發布的“聲明”仍然在其官方網站(www.cipb.org)上掛著。聲明全文如下:“根據反映,第二屆中國國際海報雙年展全場大獎作品有抄襲嫌疑。雙年展組委會決定將對此事展開慎(注:原文如此)密調查。”而朱巖岳铤而走險的“民告官”(10月31日開庭審理),直到12月20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才公布了原告敗訴的一審判決結果,原告迄今尚未表示提出上訴。不出筆者所料的是,目前看來這兩起事件在處理上都越來越暴露出“無疾而終”、“不了了之”的跡象。
坦率地說,這兩次涉及設計作品“抄襲”的爭議從一開始似乎就注定是沒有確切結果的。但由於兩個“抄襲”事件在性質上並不一樣,我們不妨先分開來討論:平心而論,“故宮院徽案”中,無論是朱巖岳的方案還是最終采用稿,從藝術品位的角度說都不屬於上佳的作品,尤其是在國內似乎是無法避免的“庸俗寓意”——這一個前提首先是無可辯駁的。進一步,盡管都采用了“宮”字的獨體造型,但最重要的創意點和表現手法都有所不同,甚至相對而言,我認為理想公司的方案的確要稍稍成熟那麼一點點,僅此而已。換句話說,即便是邵柏林和理想公司看過了朱的方案,但的確沒有抄襲朱氏最核心的“創意”(即“GG”的變形),而據筆者的個人經驗,以“宮”為單體造型的方案這個並不是很難想到的一個角度在應征作品中還大量存在。因此——恕我直言——即便是朱巖岳等原告提出上訴,講求“誰主張,誰舉證”的二審法院,極有可能再次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判上訴人敗訴,並且還要自行承擔高額的訴訟費。
而“林洲事件”中兩件作品(原作和被指為抄襲的作品)的近似程度則要遠遠高於“故宮院徽”,其創意甚至形式簡直如出一轍。相對而言,盡管林洲的作品在作者自己所說的“圖底關系”方面處理得更為舒展,甚至賦予了實用性的附加涵義,但必須承認這幅作品最吸引人之處恰恰就是這個竟然如此“重合”的創意!筆者在直覺上判斷這兩件作品中晚生的那一件至少應該是有意無意地受到了前一件的啟發,但同樣也是無法舉證的。筆者只是根據個人的創作經驗感覺到在現實中,我們的確經常碰到“創意撞車”的情況,可表現形式上也如此接近的確很難令人信服。
不過這裡筆者更想說的是,如果我們還承認設計是一門藝術的話,那麼“獨創性”無論如何還是應該加以強調的。但這裡所說的“獨創性”不僅僅是對於抄襲的抵制,還應該包括徹底的個性化、自我化,換言之,其創意是出自個人的獨特經驗、知識結構和文化積累,應該是從根本上排除“與他人撞車”的可能的(這當然是理論上的理想敘述)。依稀記得兒時讀過的《三國演義》裡的一個情節:曹操以《孟德新書》見示“過目不忘”的張松,後者竟當場背誦一遍,誣稱曹操抄襲“蜀中小兒亦會背誦”的戰國無名氏的著作。曹操一面自忖:“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一面將《孟德新書》付之一炬(大意,其中的細節回憶有可能受到電視連續劇的影響)。筆者這裡所稱道的當然不是曹操的剛愎和武斷,但他標新立異的決心或許是值得設計師再三品味的。換言之,此時筆者最希望對林洲先生和“故宮院徽”的設計者們說的是,最獨創、最優秀的藝術設計作品,應該是不怕有“和別人撞車”的可能的,否則就應該從作品本身去發掘進一步完善的可能。盡管我尊重朱巖岳先生為中國設計師著作權的爭取所作出的努力,但我們也只有通過加強設計師的自律來確保設計共同體的尊嚴。具體到 2005年這兩大設計事件本身來說,看來除了當事者向公眾坦誠相待之外,無論是法律還是其它的業內人士恐怕都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只能借用林洲先生本人的話——讓“清者自清”了。
二、“福娃”:中國形象設計之痛
2005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五個“福娃”的頒布,不僅對於平面設計界內部,還是全中國來說都是一件大事,確切地說,我們不能夠僅僅在平面設計乃至藝術本身來討論“福娃”所帶來的一系列的話題。在2003年公布了令業內人士大跌眼鏡的“中國印”之後,本應2004年與公眾見面的奧運會吉祥物則一推再推,終於在“奧運倒計時1000天”的2005年12月11日夜公開。緊接著的是媒體上鋪天蓋地的關於韓美林、吳冠英等主創者加班加點修改定稿的感人經歷,的確讓人無法不對設計師及北京奧組委的工作表示最起碼的敬意。不過盡管如此,必須承認工作的勤奮與否並不是衡量作品藝術價值高低的必要條件,我們還需要堅持藝術和學術標准的設計批評。“福娃”及此後專業設計師的大量批評,依然反映出許多值得人們思考的設計體制和設計意識問題。
在吉祥物公布第二天,筆者曾試用淺近文言作《“福娃”之惑》一文,作為對於“福娃”本身的設計批評,將其藝術上的缺陷概括為以下四點。此文除了網絡之外未用作公開發表,不妨在此稍加轉錄:
所惑一者,以“動物形象卡通化”為吉祥物設計思路,莫不嫌狹隘乎?吾國歷史垂三千年,可做吉祥物之圖形圖象夥矣,陶盆人面圖形(吳冠英本已有此創意),敦煌壁畫圖案,俱可少加修飾而新用焉。且藉此良機,展示我中華文化,何樂不為?視今日之五“福娃”,吾國“動漫”界人士構思與表現之貧乏於此暴露無遺,徒聊下策耳!
“五行”、“五環”之喻,乃至“諧音連綴”之所謂“創意”,俗便俗矣,尚非不可也。吾所惑者二,在其“分類標准”:“火”與動物並列,且“人畜共和”,此形式邏輯之大忌也!若夫以動物分,則動物形象俱應見於頭飾。然此五“福娃”者,其五有四貌似為人種,蹴然配之以一“熊貓”頭,其笑我中國人與動物同類乎?況以動物為分類標准,則“門綱科目”亦應對等,若“藏羚羊——白鳍豚”則可,斷不可“藏羚羊——魚”並列。個別美術工作者不通此理尚可諒,諸多“專家”竟無人質疑,此實國人邏輯思維欠缺所釀之大悲劇也。
若夫以單體形象論,則“熊貓”一圖尚稍可觀,然亦不得與吾國1960年代前後之眾多動畫美術造型同日而語。且可推敲精簡之處尤多,猶以額頭所佩一“中衣”為甚。其余四玩偶,除用線外與“熊貓”俱不和諧,似非一人所畫。且造型雷同,簡陋庸俗,以此蠢物何以與雅典奧運等優秀吉祥物設計並炳史冊,更遑論承續吾國早期動畫學派之傳統?歎歎!此吾所惑者三也。
“吉祥”也者,非徒為幼兒所設也。北京奧組委以是圖訴求於嬰幼兒,此惑四焉。吉祥物圖案本藝術創作,文化符碼,非徒玩具之物,然竟“幼兒評審”以贻笑大方,總“可愛”為“第一原則”,其謬大矣!且吾國今時之嬰幼兒,文化環境嘈雜,審美教育不力,吾輩安復求其判斷力可乎?君不見今日少年趨“藍貓”之若鹜哉?!此卡通形象,遑論妍媸,其境界下舊時之水墨動畫不知幾千裡也,少年因審美教育與批判
- 上一頁:那些一字千金的廣告詞
- 下一頁:數字化境遇中的漢字設計問題